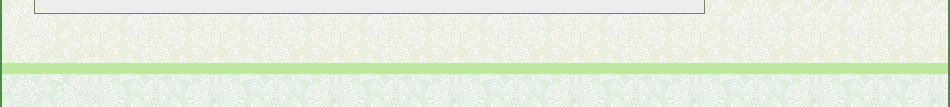2015年9月7日,从黄光利在微信朋友圈发的《讣告》得知,洛地因癌症晚期医治无效,已于6日晚与世长辞,终年86岁。就我个人而言,失去的是一位鲠直、豪爽、肝胆相照的朋友,但中国戏曲界却从此失去一位立论奇诡、自成一家、理崛辞新的精英人物。
我和洛地的相遇还真有点传奇性,1957年,我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一首长诗《怀念你,绿色的边疆》,占了两个版面,翻过一页,是署名“洛地”的另一首长诗《跳花灯》,语言隽永清新,颇具灵气,便萌生了想交朋友的想法。通过编辑部牵线,终于联系到了洛地。谁也没有料到,才通了一封信便大难临头,反右运动席卷整个中国,我和洛地都榜上有名,在劫难逃。
1982年冬,我在《浙江戏曲研究资料》发表了论文《魏良辅辨》,却未曾想到该刊的主编就是洛地,还给我寄来热情洋溢的信。1983年初夏,浙江省文化厅在普陀山举办拨乱反正后的首届戏剧座谈会,二十多年前被扫地出门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欢聚一堂,那种惊喜、激动、痛哭流涕与欢歌笑语并存的场面很难用语言形容。我的一大收获,便是此时认识洛地。当晚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省文化厅副厅长钱法成和著名编剧顾锡东在宴会上致词,号召参加会议的剧作家们用诗词的形式来记述这一历史时刻,当晚我就填了一阕《沁园春》:
碧海天青,佛门香贵,高阁簟凉。喜名山荟萃,戏文子弟;禅楼欢聚,顾曲周郎。 论剧神驰,谈诗肠热,好酒何妨醉一觞。流连处,是春风意气,秋水文章。 酒酣互 探行藏,问二十年间底事忙? 道补天乏术,挥锄荒野;沉肩有力,挹汗农桑。两鬓飞 霜,壮怀犹在,好掣铜琶唱大江。休嗟叹,且纵情一笑,力挽夕阳。
1984年,我调回市文化局艺术研究室,接编《南戏探讨集》,同时还成为《中国戏曲志?浙江卷》温州条目的责任编辑。洛地则成为《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主编,我和洛地的接触更显频繁。温州市文化局的经费极其困难,《南戏探讨集》的出版难以为继,省艺术研究所所长陈西斌要我与洛地商量,洛地同意由他主编的《浙江戏曲研究资料》专门为《南戏探讨集》出一辑。温州拟举办南戏学术研讨会,也因经费掣肘难以实施,经过洛地协调,陈西斌同意,省艺术研究所拨给七千元,终于在1987年成功举办温州市首届南戏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选举王季思为名誉会长,徐朔方为会长,洛地当选12名干事之一。
九十年代以前,省戏曲志总编史行(前文化厅长)每年都要召开一到两次会议,每次开会都会与洛地见面,互相交换一些资讯,如他把胡忌发现的元刘埙关于“永嘉戏曲”的记载告诉我;我则把《杜隐园观剧记》中发现的刘埙《义犬传》告诉他。九十年代以后,我和他都退出“江湖”,碰面的机会相对减少,偶尔相见,大多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有时我们就互相传递“伊妹儿”,也经常电话问候,他每出新作,都要寄一本给我。
洛地性格孤傲,脾气暴烈,有事没事都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但他却是个一竿子到底的直性子,就像一个大炮仗,放完便归于寂静。当面吵得不可开交,过后便烟消云散,从不记仇。我们两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有时也会脸红脖子粗,但过后一切如常,相处还算比较融洽。我每次去杭州,他一定要我在他家嘬一顿,要是不遂他的愿,他马上就会面现不悦之色。也许就是他的脾气古怪,因而朋友不多,我倒成为他可以促膝长谈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他的夫人林颖宁患有更年期综合征,经常出现神不守舍的症状,洛地却能细心呵护,体贴入微。林颖宁去世后的十多年中,家里的灵堂一直存在。
洛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钻研戏曲理论,三十多年来斩获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词乐曲唱》《戏曲与浙江》《戏弄?戏文?戏曲》《中国戏曲音乐类种》《说破?虚假?团圆——中国民族戏剧艺术表现三维》《周传瑛昆剧生涯六十年》《魏良辅?汤显祖?姜白石——曲牌与曲唱的关系》《词体构成》《洛地戏曲论集》等。由以上作品结集的《洛地文集》已出版到第五集。此外,他主编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共有十多个分卷,总字数在三百万以上。
在中国戏曲学术界,洛地是个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学者,他不拾前人牙慧,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著作大都是与众不同的自说自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洛地此生无缘立雪学界,只得自学自问自思自答。”他在《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缺憾》一文中,以敏锐的目光透视近百年来中国戏剧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如中国戏剧的起源应该是扮演而不是歌舞,为此他对王国维“歌舞演故事”的名言作出不同于一般的解释;又如,他认为戏剧的本义是扮演,中国戏剧的研究应该是戏剧的本体而不是曲腔,而当代的许多戏剧史实际上记述的都是曲腔史;再如,当代戏剧史往往偏重作家与作品的研究而忽视戏剧的结构与体制等等,可谓独具只眼,针针见血。此外,他提出戏剧艺术表现三维:说破、虚假、团圆,六个字对戏剧艺术形态作了高度概括。
总之,洛地的戏曲理论大都发前人之所未发,确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者们偶亦对洛地的一些观点私下议论,觉得某些论据的定义失之粗糙,不够精准,逻辑不够严密,但要提出反驳,却又不知如何下手,因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洛地自说自话的理论提出补充或反驳。我认同洛地的某些观点,如“戏”和“曲”的关系是“文主乐从”以及宫调系统在曲牌应用中没有实际意义等。
洛地走了,中国戏曲学术界的各种会议上不会再听到他那一口浙江普通话的高谈阔论。我总觉得有一种遗憾拥堵心头:他是当代唯一全方位梳理中国戏曲史的学者,然则是非得失迄今无人评说,客套的说项并不代表真理,洛地的悲情也许就在于,当真理的检验还没有启动之前,他就匆匆撒手人寰了。 (原载2015年9月16日《戏文》)